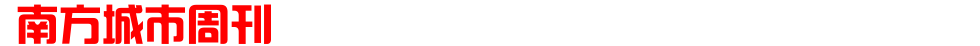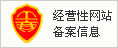邢淼特别讨厌冬天,讨厌冬天灰蒙蒙的阴天,讨厌光秃秃的树枝,讨厌空气里弥漫的冷冽。
等了许久,终于等来了绿灯。和着人流,邢淼走过斑马线。马路对面那家面包店的飘出的浓香紧紧地拽住了她的鼻子。中午,寄宿的女儿就会回家,吃过午饭她就得马不停蹄地去上补习班,买个面包给孩子当个点心也好。邢淼从刚出炉的一众面包中选了女儿最喜欢吃的肉松面包,就在她排队等着付账的一会儿,透过橱窗,她又瞥见了那位老妇人。
她晃悠悠地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厚重的棉服包裹着瘦小的身躯。蓝色的卡其布帽一如既往地耷拉着,宽大的帽檐遮住了她大半张脸,也遮住了刀刻般纵横交错的皱纹和一双近乎呆滞的泛黄的眼。她就这么蜷缩地靠在橱窗边坐着,脚下摆着一个把手缠着布条的竹篮。隔得远了一些。邢淼看不清今天那篮子里摆了些什么货物,只能借助橱窗透出的斑驳的灯光看到一些黑乎乎的东西。
坐在那里一定很冷吧?穿着长及膝盖棉服的邢淼心想,自己就在街上走了一小会儿都觉得寒意渗骨,更别说寒风中夹杂些许的雪籽已开始向人袭来。思忖间,邢淼就见几个高中女学生跺着脚围在了老人的身边,不一会儿,她们便嬉嬉笑笑着买走了几包不知道是什么的货物。
老人咧开嘴笑了,那张脸像极了一张蜡黄的开裂的蒲扇。有那么一刹那,邢淼竟将老人与自己母亲的影子重叠在起来。一样佝偻的身躯,一样布满皱纹的脸庞;一个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安享晚年,一个却在用雪鬓霜鬟与生活一争高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恐怕就是邢淼此时的心境了。
篮子里货物已经不多了。走出面包店,邢淼还是在老人那儿买了了一包酸枣糕。当邢淼与老人那双干枯的双眼对视时,邢淼莫名地一阵心悸。在老人的注视下,邢淼几乎是落荒而逃。邢淼不想听到老人说那一声“谢谢”,虽然这两个字轻如鸿毛,却如同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的重一样令人畏惧。邢淼畏惧于自己的渺小,只能卑微地用一点点的金钱去弥补能力有限的遗憾和维护这位自食其力老人的尊严,邢淼更畏惧于早已知晓真诚和真诚本应是同样的分量,却在各自心理的天平下分出的胜负。
不知从何时起,细碎的雪花纷纷扬扬地登场了。一点、两点、三点……落进衣领,凉丝丝,冷泠泠。对于在室外待得久的人,这点冷和冻已造不成什么威胁了。可对于她呢?邢淼忍不住,回过头看向老人的方向。竹篮上的布条,借了风,飘啊飘;板凳上的老妪,入了定,摇啊摇。邢淼扭过头又看向喧嚣的世界。有璀璨的灯光,有绕梁的歌声,有诱人的饕餮,有欢快的人们,还有等待卖完商品才能回家的老人。
邢淼很希望自己能拥有办公室那群在商场横扫一切的女人们的气魄,扯出几张大钞把老人剩下的货品买完。可是生活,容不得她有太多的善心。邢淼忍不住轻叹一口气。再过一个星期,女儿就要期末考试了,辅导班的家长群里已经发了好几次续交补习费的通知,早点交钱,可以安排一个好的位置,过了这个假期,女儿的又要交学费了,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万。房贷和车贷,再加上日常的开销,对于邢淼和丈夫这种拿死工资的家庭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母亲年岁渐长,三天两头要去医院看看,住院和疗养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些邢淼觉得都还勉强能应付,但她最忧心的是丈夫的身体状况。
邢淼的丈夫康福强是一名交警,平日里的工作岗位就是刚才她经过的十字路口。穿过川流不息的车辆,邢淼看见站在交通岗台上的是一名年轻的警员。他穿着整齐挺拔的制服,每一个手势都果断有力。在他的身上,邢淼看到了丈夫年轻时候的模样。这两年,丈夫康福强的身体大不如前。本来很魁梧的身材日渐单薄,宽厚的肩膀也瘦削得像一把拉开的弓,不到五十岁的他发际线都快到后脑勺了。邢淼不止一次地劝说康福强去医院做检查,可他就是不同意,倔着脾气说自己没事。邢淼想起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文章,说人要是无缘无故地消瘦,只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可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对付丈夫的执拗。在这个家里,唯一能对付康福强的只有女儿了。别看丈夫平时严厉得紧,在女儿面前却是不折不扣的“女奴”。
邢淼折回来,站在了马路的边沿,她看向街对面的岗楼,希望能看到丈夫的身影。岗楼有好几位交警出出进进,却没有看到康福强,倒是有一位老交警注意到了邢淼的注视,甚至冲着她的方向笑着招了招手。邢淼想,这位应该是丈夫的同事,要不怎么会认识自己。可他叫什么名字呢?邢淼盯了他半天,楞是没有想起来,看来只好回家以后问问丈夫了。
天可真冷!
邢淼吸了吸冻得有些麻木的鼻子,又转身朝家里走去。得赶在女
儿和丈夫回家前把空调打开,母亲一人在家是舍不得用电的,再冷的天,老人家都只是守着一个电烤炉,还是开到最小档。再把昨晚炖的羊肉汤煮开做成羊肉火锅。女儿最喜欢吃羊肉了,老人喜欢喝汤,丈夫和自己都不挑食,也喜欢吃火锅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事物。总之,这么冷的天,没有什么比一家人齐整地围在一起吃顿热乎乎的饭更幸福的了。
一想到这,邢淼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眼看着又经过那位卖杂货的
老人的面前,邢淼忍不住冲着老人笑了笑。“真希望她也能早点回家呀,”邢淼心想,“真的抱歉,能力有限啊,下次再帮她买点东西吧。”邢淼忍住了再次购买的欲望,不再左顾右盼,向家里匆匆走去。
而在邢淼的身后,老人却渐渐坐直了身子。她定定地看着邢淼渐
行渐远,突然,老人干涸的眼里涌出的泪水,那泪水瞬间填满了老人脸上的沟壑,打湿了漏在帽檐外的几缕银发。半晌,老人伸出枯槁的双手,紧紧捂住了嘴,她想防止悲伤从嘴里溢出,然而,那些呜咽伴随的悲恸让那瘦小的身躯止不住地颤抖,像一只在寒风中哆嗦的鹌鹑。
从岗台上换班下来的刘志急匆匆地朝岗楼走来。他看见队长赵青云一动不动地站在岗楼的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街的对面。刘志顺着他的目光看到的正是这一幕。刘志疑惑地问道:“赵队,康队的爱人又来了?”赵队长紧绷着脸,点了点头。刘志不是第一次看到老人,他也最看不得老人的悲恸,他忍不住问:“康队爱人的病还没有好?”赵青云长叹一口气:“哪有这么容易!两年的时间,小邢先后失去女儿和丈夫,这个创伤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也是啊,她是失去了记忆,但总归是活在希望里,就是可怜了康队的岳母。”刘志怜悯地看向老人,“一大把年纪要承受外孙女车祸,女婿病逝的悲痛,还要经历亲生女儿的失忆,老人家才是最难熬的啊。”刘志一想到老人每天坐在邢淼徘徊的路口,一边靠卖点不值钱的货品补贴家用,一边希望能唤醒女儿的记忆,心里便一阵抽痛。相见而不相识的痛苦恐怕是人世间最大的难、最痛的伤了。而这些伤痛,老人一背就是两年。想到这,刘志不禁湿了眼眶。
“去!” 赵青云掏出钱包递给刘志,“去岗楼里找个人,帮老人家把篮子里的东西都买回来!”刘志一把推开赵青云的手,跳下楼梯,边跑边说:“赵队,天太冷了!我自己去!”
赵青云看着刘志飞快地跑向街对面,远远地看见他和老人交谈着,看着他和老人在拉拉扯扯,看着刘志抱着一堆的东西往回跑,看着老人在他身后急急地喊着什么。赵青云深吸了一口气,他抬头看向天空,心里寻思着,今天下完了雪,明天总该放晴了吧。(湘潭市金庭学校/段敏)